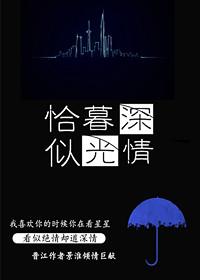第164章 奔逃
花木公子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叔叔小说www.kelibujiqi.com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老者的谈话还在继续,风菱隐隐中随着他的故事,神识里闪现过一幕幕模糊的片段,那些片段压抑着她的心神,好像有人掐着她的脖颈,让她窒息。
毕竟,她也是亲身经历了那场水患之人,可是她却一点也想不起来,只有偶尔恶梦来时,会听到大水的狂啸之音,还有黑暗中有人在说着什么。
但,她到底为什么忘却了这段过往,忘却了自己儿时的记忆,她想不明白,每每想起,就好似会揭开一道她不想直面的疤痕。
面馆外的北风仍旧吹动着,天上的黑云压了下来,想是要下一场大雨的先兆,只闻“砰”的一声,街道上的一块老旧招牌被风搅着,掀倒在地。
风菱被这突兀的声音惊了一跳,从刚刚的思绪中回过神来,继续听老者道:“当时老朽带着孙儿一路仓皇逃窜,不知方向,直到见到从黍实主城北诏城来的一队官儿,他们稳定了秩序,一路寻着四窜的难民往南面的山丘上迁徙,老朽才活了下来…”
“再后来,我们刚到南面的一座山丘,就见到从北面突然出现了一道奔腾的江河,好像真从天上倒挂下来的,一下淹没了山丘之下的村落,什么东西都没有了,真的就这样全没了,全没了,全没了…”老者的尾音一直在不停的回荡,带着叹息的哀伤,烙印在风菱的心底。
她好像看到了大河奔来,一瞬间吞没了一切的画面,生灵被河泽吞没,眼中的家乡消失得无影无踪,一幕幕零碎的记忆在神识中作祟,风菱忆起了一个画面:
那是一个七八岁的女娃儿,对了,长得水灵小巧,那是她自己。
那个一身血渍,沾满泥土的她站在一个山崖之上,看着大水肆意翻涌,淹没了一个城镇,眼前的震撼让她步步后退,她奔溃地哭着,边退边自言自语:“不,不是真的,不会是我引来的妖怪,不是我,我不是不详之人。”
风菱忆起这个记忆,身子猛的一震,手心浸出了细密的汗湿,她手指止不住颤抖,连说话的声音都带着起伏的喘息,忐忑地又问了一句:“那…那老人家可知,当年大水是怎么来的?”
老者耸了耸肩,摇头道:“不大晓得,不过往南走的途中,听官爷有谈起,说是人祸,是妖怪作法生出的大水,但后来来到京城之后又说是天灾,谁也不晓得哪样作得真。”
说着,老者叹了口气:“也是黍实不幸,又是大水,又是战乱的,不过好在,大水来得及时,倒把战乱给平息了。”
老者谈到此处,先前面馆的人也还是忍不住加入了话题,多是谈及北族的战乱。
说实在的,这些百姓谁也没见过北族,连怎么打起来的都不知道,只知道大水来后,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,因淹没了黍实九个郡,再加上黍实州旁的蒙乌州的以北两郡,刚好形成了若大河泽,阻断了北族进攻的通路。
他们絮絮而谈,完全没注意到风菱早已听不进去了,她恍恍惚惚地站了起来,连先前问家人之事都全然忘记了,或许她也不用问了,因为她想起了一些极少的,最不想记起的事情,她的父亲大概、或许已经不在了,何必再问。
风菱跌跌撞撞的走出面馆,扶着面馆外面的泥墙,走了几步,却觉得脚下松软,跌跌撞撞的找了个矮脚坐下,用颤抖的双手捂住了唇,靠紧了墙面,仰着面,竭力让自己不哭出来。
冷风刮过风菱的面颊,若是她能感觉到痛觉的话,她一定会觉得刺痛的疼,但这些都不大重要了。
风菱伸出手,颤颤巍巍地将手指移向脚踝处,拨开足上罗袜,一道黑色的勒痕在脚踝处清晰可见。
这道痕迹风菱是知道一直有的,可是她并不记得它存在的原因,直至今日她才忆起,就是水患当时留下的。记忆飘渺,飘渺到七八岁那年,原来她是那年走失的,而在那一年发生了许多事:
————
一个漆黑的夜里,风菱睡熟时感觉到了一阵颠簸,她揉着眼睛醒来,自己正身处一架马车之中,车中挂着绸缎帐幔,像是一富贵人家的车架,记忆中的风菱对这辆车驾很熟悉,应当是她自家的车銮。
风菱醒来之后,见身旁没有熟悉的人的身影,只有随身带着的白幡,又听见外面赶车人的声音和马儿嘶叫的急切,她心下很担忧,于是猛地拉开了车帘帷幔,车前有两人,一位马夫,一个身穿甲胄的男子,她对着身穿甲胄、抱剑侧坐的男子问到:“爹爹呢?”
那男子回过头,此人面色如鹰般犀利,眼神肃穆,像极了一只猎豹。
他见风菱担忧的神色,没有安慰的意思,只沉沉地认真道:“小姐,老爷让我给小姐带话,日后他不能陪小姐了,他要留下来,守护别人家的孩子,他让小姐好好活下去,小姐绝对不是灾星,来日小姐一定会遇到守护小姐的人。”
男子说到这里顿了顿,片刻之后,才道:“另外,还有一句,对不起。”
当时的风菱很小,男子说的话,她听得懵懵懂懂,可是她从他的话中听到了悲伤,无比悲伤,好像是诀别的话语,她觉得她可能今日起就再也见不到父亲了。
男子见风菱颤抖的唇瓣,眼中若隐若现的泪纹,这才松了松紧绷的面颊,掏出了一把精致的匕首,那匕首异常精美,刀鞘上坠着鸽子蛋大小的琥珀,镌刻着兰花图纹。
男子将匕首塞进风菱的手中,见她一动不动地盯着匕首,男子叹了口气,又道:“小姐,您把匕首收好了,属下知道您出生书香门第,不喜舞枪弄棒,但兴许用得上,这是老爷留给小姐防身的。”
风菱捏着匕首,却好像听不到男子的话,她觉得天都快塌了。
她爬向车銮中,拉开车后的帘子,往马车行来的路看去,顺着小径上碾压出来的马车车痕寻找家的位置,可惜不知是家太远,还是夜太黑,她看不到,只能眼泪奔流地冲着远方大喊:“爹爹!”
没有回音,只有马蹄的声啸。